火。被裹在红纸下,透散出来。映着重重叠叠的幢幢人影。蛾子一头扎上去。卟的一声,淹没在车马与人言里。纸灯笼颠得摇晃。别家的某某大人从它前面借路蹚过,遮了一半的光旋动着,从门口的石狮子转到我的眼内。陛下,天凉露重,上轿回宫或者进屋再续一壶吧。免,免。朕再看看,就喜欢这热闹劲儿。于是便看着百官……百官,哈,简单的数量与身份整合,会是如此讽刺的用词。于是便看着,参与天锡王府晚宴的这几十名官员,鱼贯而出。朕就看看,卿家如常便好。怎敢当真如常,照例还是一一与我拱手行礼,掀起各自的轿帘,不敢与府主人多作寒暄,便起轿各自回程了。北辰胤隐在朝内的心腹企图留到最后,我凝视他,他不得不同我拱手,侧目与党首交换了眼神,无可奈何地轻轻点头,只得也上轿离开。或许他们达成了什么改日再议的共同体认,我揣摩着。车马各行各轨,惟余那乘舆顶用金的轿子。逐渐安静了,剩下堂内隐约传来的叮叮当当,仆从在收拾碗碟。我回头看他。北辰胤,你不送我?
天锡王,不送送朕?与话语一同漫出一扑酒气。他便来搀我,我说倒也不必,朕又没醉。说着却沉沉地往他身上靠。他扶我上轿,见我实在醉得厉害,吩咐了自己的一名婢女随同看护。我努力辨认她的样貌,应当不是先前宴上我抽了一巴掌的那个。于情理来推应也不是。
看着婢子,北辰胤应也是同样回想起了席间我的乖戾无常。皇……儿何时起这样的?
你还不清楚吗,我心想着,先是舌尖矫作了一个爆破的气音,知晓他听到了,再假作不甚情愿地将称谓改口:皇叔难道不清楚嘛。
听太后讲,你小时便惧恶这些下人惧恶得厉害。
我或许当真是有些醉了,醉得壮胆,噎他:到底是太后讲的,还是秋玲嬷嬷讲的?
他看向门前的纸灯笼,一晃,两晃,明了,暗了,就连它也瑟缩。
好啦,果真是如此。凰儿便也安心了。我噙着笑,将他的疑心一并拥住,以不带锋芒的酒气晕染开暗藏的杀意。
殿下又来啦。女官领着尚不及她胸前的太子入殿,任由小儿直奔到太后身前。这都快要总角了,怎地越长越粘人得紧?太后将打发时间的女红针线压好,抬手搂过从小带大的皇子。秋玲别说了。怎么,还是害怕?潭子已经填上了,母后也请了道士给东宫驱了邪,那个不小心的宫女不会再来找凰儿了。我将头埋在她怀里,过一会儿才闷闷地说:还是觉得怪怪的……她是不是想回来讨我要赏赐,或者补偿?自她走后,总觉得宫里似乎总有东西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什么东西不见了?都是一些首饰,簪子,璎珞,连前日想送给母后的步摇也消失了,找了许久也找不到。太后和女官对视一眼。也许不是她来找你……罢了,这事还是母后来解决吧。真的好怕。在此之前,凰儿都不愿回宫了。这怎么行?哎呀,那好吧,让秋玲嬷嬷替你回东宫点几个宫女过来照顾你。不要,怕的就是她们,觉得她们都好像她……
陛下。轿子平缓而规律地摇晃着,从王府跟过来的婢子问我:陛下,要不要把帘子放下?看陛下方才睡过去了,夜风吹着,怕会伤寒。
所以你将朕叫醒,就为这种事情?婢女瑟缩地犹豫着,不知是不是该立即磕头认罪。……算了。我压下心中习惯性的烦躁。放下吧。
第一名宫女死于假山后的幽潭里,很安静。我将她的头埋进水里埋了半刻钟,她初时还想挣扎,越挣扎越是呛水,呜咽着徒劳耗尽她剩余的空气,或许有眼泪也一瞬便在潭水中化开了。我斟酌着她肢体动作的逐渐微弱,到最后只剩本能的抽动,便将她完全推了下去。回来喝茶练字练了大半个时辰才又去找她,再惊慌地跑回,语无伦次地向宫人指引方向,才让人将她捞上来。第二名宫女死于偷窃宫中财物,很吵嚷。女官秋玲带着人将东宫搜查了底朝天,终于在偏房的暗格里发现了那枝步摇,住在那处的宫女拒死不承认是她藏的,为证清白将可疑人选一一指认,互相揭发出了不少鸡毛蒜皮的秘辛,太后趁机将东宫从下到上整治了一番,换人换了七七八八。只是到最后也没有坚实的证据证明是别人所藏,还是将她逐出了宫去,太后对我讲的是只是逐出了宫,后来了解到确实是私下处死了,这才稍放了心。第三名宫女得知了当初那枝步摇原来是我放进的暗格后简直要疯了,质问我这般无端地疑心她们到底疑心了个什么?就因为和同龄的王孙子弟难得聚会的时候被北辰伯英笑话了一句豢犬不食净肉,就觉得大王爷一派要害你、派了眼线监视你?并不是每朝都有话本上那么复杂的宫斗!我被驳斥得恼羞成怒,骂她:哪里有这么复杂的因由,只是因为你们这些奴才碍了我的眼,而已。那是我初次这般称呼她们,话一出口仿佛听到了窗纸破裂的一声闷响,声音却好似遥远隔绝了,隔了一层粗糙的琉璃,连她们的面容也模糊到难以记认了。我拔出梨木架上练武的剑贯穿她的胸口,她反而平静了:至少婢子不是殿下所怀疑的某人某派的眼线,也可以想象先前这东宫内的很多亡魂,都是殿下错杀。殿下,就算这宫中真有想害你利用你的人,那也想必是对你极讨好的,而不是我们。我不想再听,添一剑割断了她的喉咙,奔出去找秋玲嬷嬷,让她转告母后有个宫女疯了,被潭水中的鬼魂上了身。
她或许说对了一半,年岁稍长后,北辰伯英应也是得了大人的教告,言辞对我谦让了许多,也未再让我如幼时那般难堪。只是那便如裹在肉里的刺,只剩隐隐的疼。更何况,我应当也是对的——既然他对我讨好了,那便如她所说,应是对我有所求的。而只有月吟荷会信我所说的。她会与我共鸣,怜惜我过去二十年风刀霜剑的岁月。
待我步上不义的九重金阶后不久,便听说秋玲嬷嬷死了。长孙佑达递给我的证据我在案上放了三日三夜,就放在手边,每抽出一沓奏折就会顺势拂过,却从未翻开。翻开之前,我让另一个月吟荷联系魔龙祭天,让他策反北辰伯英……不对,让他试探北辰伯英有无反心。过几日月吟荷回我,他确有反心,只是不知当如何下手。瞽物。我骂她。他不会就去教啊!教他何日何地起兵,何日成事。她怯生生走后,我烦躁地揪扯编好的碎发。原来他竟是如此驽钝,如此蠢材是如何当年往宫中加派眼线予我的?我不敢去想了。好在他到底是有着反心,诱他起义失败将他擒杀,如此便死无对证了。也不知这对证是向何人对证。至此我才翻开秋玲死因的奏折,不过是又一层未曾料到的风刀霜剑而已。
陛下。
陡然惊醒,反手将簪中短剑抽出刺去,刺得一声满室零碎,醒酒汤并着瓷碗迸了满地。没醉的人,怎用醒酒?我抬眼望去,好在伤的是自己的宫女,天锡王府的那名婢子已经走了。请君入瓮前,不宜横生枝节。
陛下,此前有没有宫人同您讲过,陛下或许有些,过于疑心了?
……滚。
只掷出一地空余的回音。宫女在说完那句前,就已经熟练地先行避走了。我也没记住她的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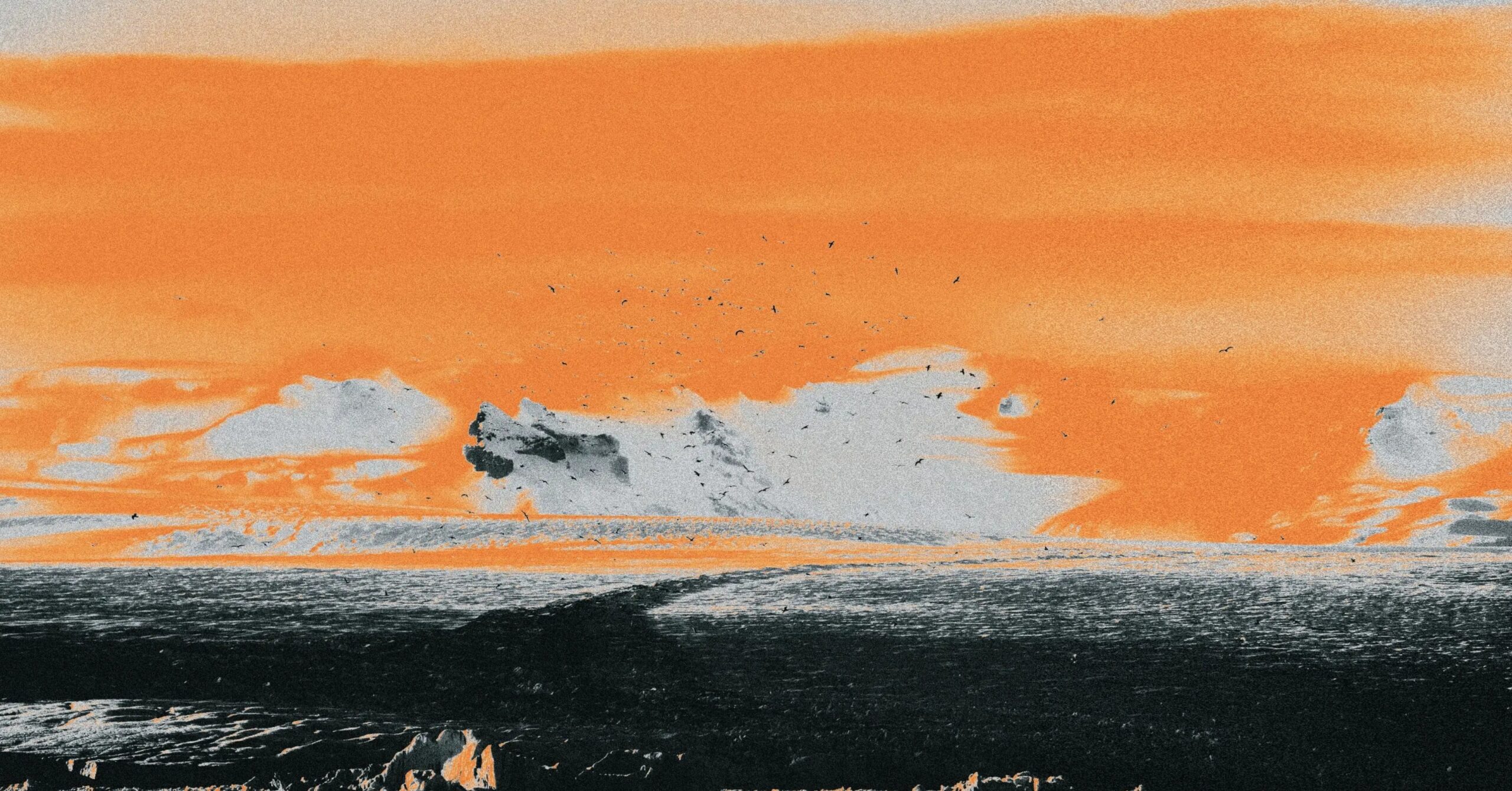

發佈留言